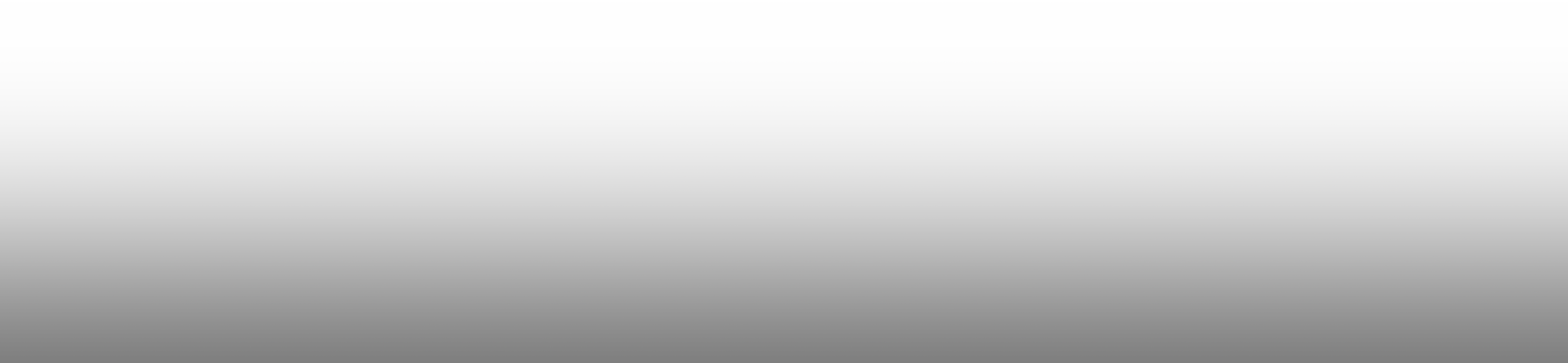我是1961年进入南开大学物理系的,从那时起,离开,重回,再离开,终于重归,在南开终老,和南开有着不解的缘分。对南开的眷恋之情深入到骨髓!
一、求学
我是1961年进入南开大学物理系的,那已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尾声了,学生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我们粮卡中的细粮(大米和白面)比例大大增加,菜里也有少许的肉、蛋之类。学生们的学习热情非常高,希望拿出好成绩,学到真本领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在我们上大课的教室(主楼的几个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大家都希望坐在前面一点。那时候,没有麦克风,就凭主讲教师的嗓音,也没有今天的视频,老师在黑板上写下长长的公式,坐在后面的同学就不太容易看清。但这样的条件也不能阻挡同学的学习热情。当时,从没有听到有同学翘课,如果因为生病或有重要的事缺课,无论如何课后都要找机会补上。再有大家都做笔记,这和今天大学生的学习方式完全不同,现在大学生很少有做笔记的。我直到在美国做研究生时都一直保持做笔记的习惯,开始掺杂几个中文字,后来就全是英文了。我的美国同学也无一例外地做笔记,有时没听清楚一个字还要看看邻座的笔记作为参考。做笔记不是纯粹重复一些内容,那些公式在教科书上都有,笔记主要是记录老师的讲解,是超出书面内容的东西,很多是老师多年来学习和科研的心得(也包括教学时获得的,特别可能是针对学生不容易理解的难点),是很宝贵的。美国大学生和研究生翘课的倒比较多,但一旦坐到教室中就很认真了。我们的学习热情也体现在寻找自习场所的“争夺战”中。
那时能作为自习场所的地方有1. 宿舍;2. 主楼空教室;3. 图书馆三、四楼的阅读室。选择3.是公认最好的自学场所,气氛好,交流也方便(到阅览室外面即可讨论)。但座位有限,我们每天早上就到图书馆门前等候,七点一开门就要冲锋一样地进到阅览室,用书包和书占据几个位子(帮同学占的,我们总是以宿舍为最小单位)。然后就去吃早饭。如果第一二节没课,早饭后就到图书馆,如果有课,上完课再回到图书馆。当然很有可能被其他学生认为我们的行动不合法而把我们占位的书包扫掉,这是就会发生一些争执。但其实自以为有理占据别人座位的人自己也占座,所以争执也不敢过分,大家都是“君子”嘛!
即使大家学习都很认真,但一学期下来,成绩差别很大。由于大家都是通过严格全国统一高考(那时全国一个卷)进入南开大学,说明在预备知识上(中学的课程)都差不多,而且智力也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为什么有的同学开夜车,有同学开早车?那时主楼的灯光通宵达旦,开夜车的同学还没走,开早车的同学已经来了。但这些同学的成绩并不理想,挂科是很普遍的(那时的考试很严)。这么用功,基础也不差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关键在于学习方法。
我记得第一年开学不久,陈仁烈教授(副系主任,负责教学)找我们几个学生座谈,就谈论学习方法。他给我的一条建议直到今天还让我印象深刻,也是我学习新知识的指导原则之一。就是给自己讲故事。他建议,每学完一章(普通物理),通过复习,认为已经基本掌握这章的内容后,把书本合上,给自己讲一讲这一章讨论的是什么,精髓在哪,有什么问题,还应该在哪方面予以修正或补充(这一点对一年级学生来说很难达到)。往往讲到一半就讲不下去了,就把书重新打开,从新阅读,特别是阅读作者写的论述(不仅仅看那些公式,而是如何理解这些公式的含义)。我这样做了,成绩显著提高。我既不开夜车也不开早车,但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原因就是,通过给自己讲物理,我懂了。“懂”这个字听上去很容易,其实这是学物理的最最根本的要求,这也像佛学中的“悟”,没有真懂,囫囵吞枣,死记硬背,及时能做习题,但实际上没有掌握物理的真谛,是走不远的(中学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是非常害人的,也是中国科学家没有走到世界巅峰的原因之一,看看当年西南联大出来的优秀学者的典例就明白了)。这个方法一直持续到我做研究生和开展科学研究之后。我也和许多同学交流过这个心得,但似乎没有得到太多的人关注。
我的这些体验和经验都包括在我的一篇教学论文中(物理与工程,2019年01 期,88页: “如何帮助物理系学生迈过高三到大一这个坎”)。
二、生活
当年的大学生都是十八,九岁到二十多岁的青年,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家庭条件也不尽相同,同学中也有一些竞争,但总的说来同学间相处非常融洽,谁有困难大家互相帮助。那时“谈心”活动是普遍的。和今天不同,我们那个时代同学间谈恋爱是禁止的。正当青年时期,男女同学朝夕相见,可以交流学习上的问题,以及政治思想上的心得,但不能谈恋爱,这是违反人性的(据说到了本世纪初还有大学对恋爱做出不合理的限制)。因而地下的恋爱就如火如荼了,毕业时这些地下的情侣都纷纷浮出水面了。
除了恋爱被禁止,其他的课余活动还是丰富多彩的。特别是运动。当年排球是大学生最喜爱的运动(羽毛球由于场地的限制,以及羽毛球比较昂贵,相应的消费不是当时学生能承担的,因而不普及。由于中学时在业余体校的训练,我是学校羽毛球队成员,但没有几个同学关注我的运动生涯),所以一到下午4:30以后六宿舍前的小广场热闹非凡,几个排球场迅速被占据,班级间,年级间还有各系之间,甚至教工队伍也参加的排球赛吸引了大批观众,几个排球明星很受“群众爱戴”,特别是女生。现在,那些热闹的撑场面似乎就在眼前,这美丽的新校园风景线,真是难忘啊!六点以后大家到宿舍水房简单冲洗,然后吃晚饭。晚饭在现在第一食堂,那时没有座位,大家就一群、一伙地凑在一起边天南海北地聊天边吃饭。那时尽管饭菜的水平和今天学生享用的有天差万别,但大家吃的很香。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没有一个人浪费一粒米!吃完饭大家各自去自习,自习后(大概九点钟吧)回到宿舍后不久就睡觉了(除了开夜车的同学),当然免不了一段宿舍的海阔天安空胡聊,包括科学,人生乃至鬼怪逸闻。紧张而有意思的一天就过去了。
三、几经风雨回到南开,就不再离开了
从61年入校,66年毕业,由于文革在学校中耽搁两年,68年离开南开被分配到保定整流器厂,直到78年文革结束后考入南开大学物理学院做研究生。我师从刘汉昭教授,从事高能物理研究。那时的起点非常低,由于我国十年动乱时期正是世界上高能物理蓬勃快速发展的十年,很多新的实验成果出现,很多新的理论,特别是规范场理论成为高能物理的基础,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那时,严肃教授(是周光昭,何祚庥的清华同学)根据一本物理报告(Physics Reports)给我们简介了这个出色至极的理论。为了增进我们关于粒子物理的知识,刘汉昭先生出面邀请高能所的郑志鹏研究员(后来成为高能所所长)和童国梁研究员来南开做了三天的讲座,使我们对世界上飞速发展的理论和实验成就(特别是新的实验发现)有了了解,这对我后来到美国从事高能物理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刘先生从事多粒子产生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水平和成绩。但由于文革的伤害,后来远走美国,再没有回到南开,我们这些学生劝过他老人家,现在的形势完全改变了,回来可以做很多事,可惜他没有接受,而老死他乡。我们深深悼念他。
79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与南开大学结为姊妹学校,明大的一个代表团访问南开。代表团中有一个国际著名物理,数学教授Hammermesh,他负责对我的面试(interview),他问了我从物理到生活的若干问题,对我的回答很满意。回到美国后就给我寄来了研究生入学的admission 和 TA (teaching assistantship )奖学金的offer。这样我在1980 年6月就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开始了我五年的学习。1985年得到博士学位后我接受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邀请成为理论所的博士后。1987年,结束了我的博士后工作,在当时校长母国光的邀请下(他是教我们光学的老师,对我有知遇之恩)回到南开开始长达四十年的教学科研工作,也是对母校的报效。
四、我对南开的一点贡献
我在南开教书,做科研,组织学术会议,带研究生虽有一点成绩但都没有值得夸耀的地方,只有几件事让我略觉得对得起南开对我的培养和帮助。
1.我最先提出实行今日物理讲座制度。这是我在美国读研究生时看到美国大学里推行这类“colloquium” 制度带来的优越性。事实上,在费曼的自传中就介绍了这个传统。确实,每个老师在自己的领域内是专家,但物理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尤其在知识爆炸的今天,没有哪个人能对多门学科有较深入的了解。然而近代大的学术成就正说明跨学科的知识往往可以带来突破性的成果。例如温伯格的电弱破缺理论就是来源于希格斯机制,而这机制正是来源于凝聚态理论。原则上,离开了自己的领域就是外行,需要有人深入浅出地介绍新学科的精神,物理图像和主要针对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我在美国学习时从这些colloquia 中收获很大。所以我就想在南开大学开展这个制度。开始阻力较大,主要是没有经费,我要靠和被邀请人的私人关系,请他们来做报告。但这种局势几年后改观了,系(现在是学院)重视这个制度,接管了管理工作,经费也得到保障。我很高兴看到这个制度在南开物理学院保持下去。
有关的一些资料参见南开“今日物理”小组发表于《现代物理知识》杂志中的文章。
2.物理的基础是实验,可以说实验是物理的根本。从古至今所有成功的理论都是基于实验观测的(也许广义相对论是例外,但不能说它真的是独立于实验观测的)。可是以前我们高能物理组只有做理论的,没有一个实验家,这就好像缺了一条腿。鉴于这种情况我在两年内收了两个做实验的研究生,但我自己不懂实验,就把他们送到高能所代培,由我的课题出钱,负责他们的安排。两个人工作都很出色,在南开(和高能所合作)拿到硕士后,都拿到美国大学的offer 去攻读博士。在美国,他们在南开受到的出色教育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美国老师普遍夸赞他们的基础知识牢固,扎实,对物理的理解很到位),他们都以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继续做博士后研究,得到各自导师与合作者的高度评价。
随后我们引进了喻纯旭教授和赵明刚教授两位实验物理学家,现在我们高能物理组就达到比较合理的配置了,但希望还能引进一些年轻人。
3.我的一个博士获得全国百篇优秀论文奖,另一人得到天津市优秀论文。他们的成就给南开大学增了光,我也觉得是做了一点贡献。我最大的成果是培养了众多的学生,他们在学术界的成就是南开的骄傲!允公允能,自强不息!